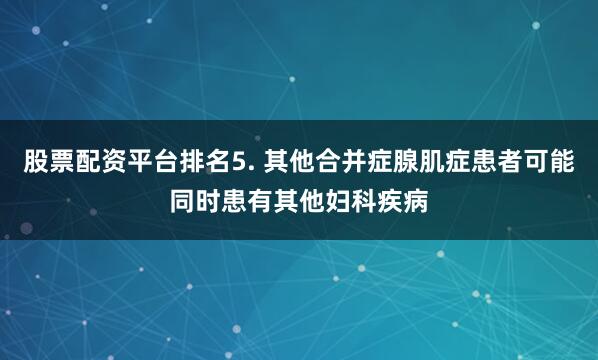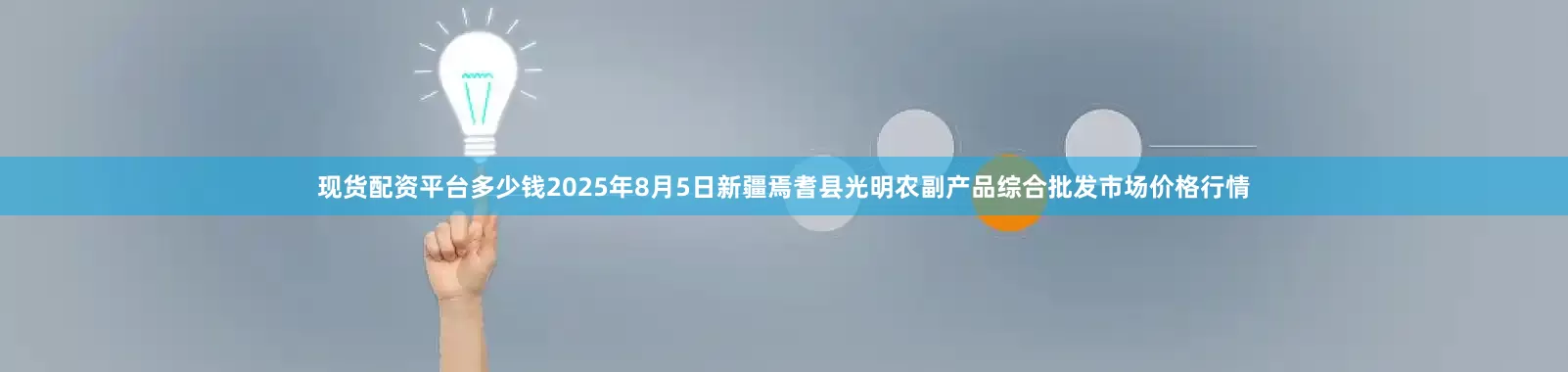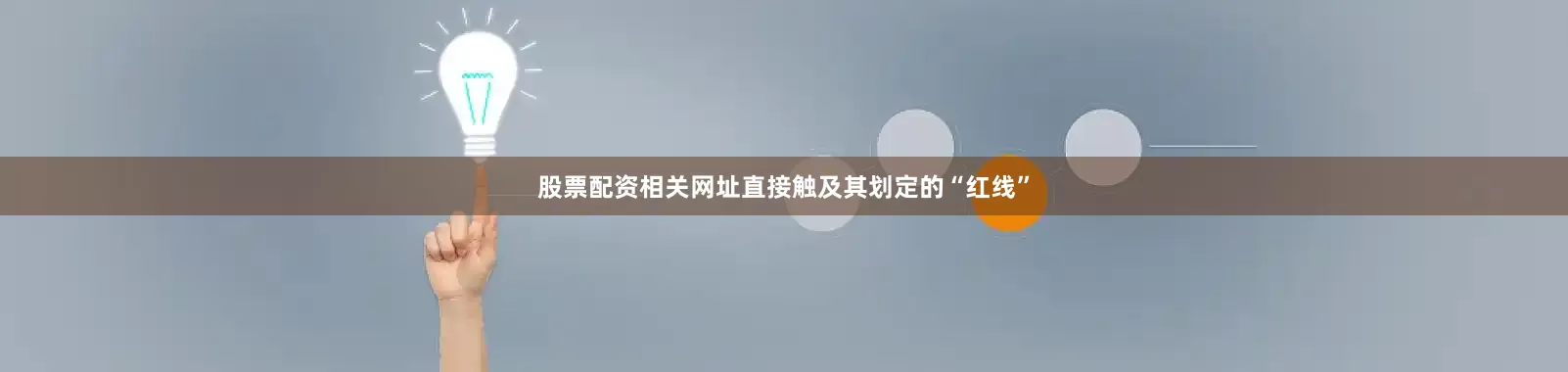
斯拉夫兄弟的血与泪:谁在乌克兰的废墟上狂欢?

一场持续三年的战争,让乌克兰的GDP缩水30%,俄罗斯的通胀率飙升至7.4%。 但当斯拉夫民族在战火中消耗血肉之躯时,美国军工企业产值增长了17.5%,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额占其总量的55%。 这真的是“正义与威权”的对抗吗? 或许,我们更该问:谁在导演这场悲剧? 谁又在废墟上数着钞票?
战争的本质:兄弟阋墙,渔翁得利

乌克兰危机被西方媒体简化为“民主对抗威权”的叙事,但历史经纬远非如此简单。 俄罗斯学者卢基扬诺夫指出,危机的根源在于三个层次: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失衡、斯拉夫文明圈的民族国家建构矛盾、以及俄罗斯内部政治定位的迷茫。 北约连续五轮东扩,将战略防线推进至俄罗斯家门口,直接触及其划定的“红线”。 而乌克兰的悲剧在于,它既是西方与俄罗斯地缘博弈的缓冲带,又成了双方拉拢的棋子。 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,西方对俄制裁层层加码,但俄罗斯凭借能源优势和“向东转”战略,硬生生扛住了压力。
战场上,俄乌双方陷入胶着。俄军凭借军工产能提升,在阿夫杰耶夫卡等地取得战术胜利;乌克兰则依靠西方援助的F-16战斗机和“风暴之影”导弹艰难防御。 然而,战壕中的士兵或许不知道,美国对乌援助中超过60%的资金流回了美国军火商的账户。 更讽刺的是,同一时期,欧洲因能源危机导致制造业外流,而美国趁机以补贴吸引欧洲企业赴美建厂。
“美式民主”的真相:盟友是棋子,战争是生意
欧洲在这场冲突中付出了沉重代价:能源价格飙升、通胀高企、经济增长陷入停滞。 但美国并未因此手软。 特朗普政府公开要求欧洲增加军费开支,甚至绕过欧盟与俄罗斯密谈,将欧洲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。 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直言:“在谈判中,欧洲只能坐在‘小孩那桌’。 ”
乌克兰的处境更为荒诞。 泽连斯基凭借犹太资本支持的电视剧《人民公仆》登上总统宝座,其幕后金主科洛莫伊斯基更是掌控着乌克兰能源和媒体命脉的寡头。战争爆发后,乌克兰高层官员中大量持有以色列或美国双重国籍,国家资产被以“租借法案”名义抵押给西方。 而乌克兰民众呢?超过350万人失业,一半能源设施被毁,重建费用高达3490亿美元,是战前GDP的1.5倍。
谁在窃笑? 资本与地缘的合谋
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披露,美国国防工业在俄乌冲突中迎来“黄金时代”,洛克希德·马丁等军火商订单激增。 更隐蔽的是,犹太资本集团长期布局乌克兰,通过索罗斯基金会等NGO渗透舆论场,将乌克兰从“反犹情绪最严重的国家”改造为“亲西方样板”。 有分析认为,这场战争的目标之一是为犹太人在中东欧建立“新家园”铺路——乌克兰西南部城市乌曼已成为哈西德派犹太教徒的朝圣中心。
俄罗斯同样陷入困境。 尽管凭借“卢布结算令”稳住了金融体系,但长期制裁导致技术断层、人才外流,国防开支激增挤压民生空间。 俄罗斯智库坦承,若战争持续,国内矛盾可能加剧。
沉默的大多数:斯拉夫民族的悲歌
当政治精英谈论“战略利益”时,顿巴斯地区的民众在炮火中求生,俄罗斯母亲们为征召入伍的儿子哭泣。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承认,战争让国家失去了30%的经济总量和350万个工作岗位。 而俄罗斯央行将利率维持在16%的高位,普通民众在通胀中艰难维持生计。
更可悲的是,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伤痕被利用为地缘筹码。 乌克兰将二战时期的纳粹合作者班德拉奉为“英雄”,俄罗斯则以“去纳粹化”为出兵理由。 双方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厮杀,却忘了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。
结语:悲剧的剧本早已写好
乌克兰危机爆发三周年时,新华社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美国大发战争财,欧洲经济遭殃。 ”当乌克兰士兵用无人机袭击俄军阵地时,美国液化天然气货轮正驶向欧洲港口;当俄罗斯新兵奔赴前线时,华尔街的交易员正在计算军火股的涨幅。 这场战争没有赢家——除了远离战场的资本与霸权。 斯拉夫兄弟的鲜血,终究只是别人账簿上的一串数字。
惠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